

● 關於木心身後美事,點滴補述
2016 , 廣西師範大學 「木心作品編輯部」把2013年開始的《木心紀念專號》一系列特刊易名為《木心研究專號》,
我在台北誠品買了本「木心美術館特輯」,簡體字版,,,
在「第三地」提出,與讀木心的人共享。
● 瓊美卡 Jamaica
在紐約皇后區,紐約市的東邊,有音譯為 「牙買加」。
![d4628535e5dde711579eb417a7efce1b9c166187[1].jpg](https://pic.pimg.tw/lingnawu/1443317538-3331648524_m.jpg)
木心先生於紐約中央公園 (分享自百度百科圖庫)
閱讀木心三十年,
起始是個隨遇的閱讀。
記憶是從聯合副刊全版面的「六十朔那梯那」,一句一句的形式,各自立意的內涵。
接著聯副版面最下方開闢一長條黑底字體反白的「一句」欄,還是木心(或者說我只記得木心)。
成篇的朔那梯那,以及日日壓軸的一句,句句雷霆,瞬間映照沉澱的人心人性,
不容我讀過就忘。
1984年,「聯合文學」創刊號,推出木心作品展,附贈的書卡中有一張木心的照片,明信片大小。
這張明信片看了又看。
1998年12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出木心的「烏鎮」。我有幸剛好讀到(存有剪報,早已泛黃) ,木心以『我不會再來』作結 。
( 1994 , 離開十多年後,悄然回家看看 )
那時理解浙江烏鎮是木心的「家鄉」。也了解生逢慘烈時代,人有機會逃離,家鄉只好留下。
一遍又一遍地讀烏鎮,更是不知道木心是誰。
他從不告訴人他是誰。
而這篇在台灣發表的「烏鎮」,被大陸烏鎮一位文士讀到,開始追蹤木心。十年後,烏鎮終於能夠盛大迎接在紐約定居 24 年的木心返回故里 ( 2006年)。時年七十九。
● 關於這個轉折,在此插入一則木心早就寫就的句:
希臘‧我
最高的不是神,是命運。神也受命運支配──古希臘人如是解,余亦如是解。命運無公理,無正義,無目的,故對之不可思,遇之不能避。
「命運」的最終詮釋:無所謂命運──在此命題上,希臘人沒收穫,余亦沒收穫。
● 作客紐約,把「瓊美卡隨想錄」後記一文提出來,源於每每在布魯克林散步,紐約地區南北向的「大道」、東西向的街、地形坡度、路樹叢林以及病弱老人,,,在在使我想起這篇後記。決定提到前面來,再次分享這位已經告別人世但留下藝術的大家。
![0df431adcbef7609ffa16c382edda3cc7dd99eeb[1].jpg](https://pic.pimg.tw/lingnawu/1443289019-2827675674_m.jpg)
當年聯合文學以這張消除背景 只有木心的照片贈送給讀者
於今取自百度百科圖庫
●2016 2月2日更正:當年聯合文學月刊附贈的木心照片是下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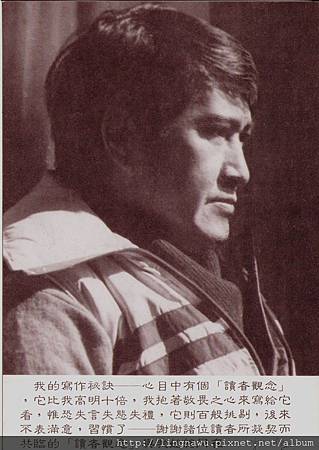
● 瓊美卡隨想錄後記 木心
還是每天去散步,瓊美卡夏季最好。
樹和草這樣恣意地綠。從不見與我同類的純粹散步者。時有驅車客向我問路,能為之指點,彼此很高興似的──我算是瓊美卡人。
有一項懇切的告誡:當某個環境顯得與你相似時,便不再對你有益。瓊美卡與我日漸相似,然而至少還無害,自牧於樹蔭下草坪上,貪圖的祗是幽靜裡的清氣。
南北向的米德蘭主道平坦而低窪,使東西向的支路接口處都有上行的斜坡,坡度不大,且是形成景觀的因素,步行者一點點引力感覺的變化,亦是趣味──有人卻難於上坡。
他推著二輪的購物車,小步欲上坡來,停停頓頓,無力可努而十分努力。成坡的路面約三十米,對於他,誠是艱苦歷程。
身材中等,衣褲淡青,因疾病而提前衰老的男子,廣義的美國人──望而知之的就是這些。車上擱著手提箱,還有木板、木框,都小而且薄。
我一瞥見就起疑問,他怎樣來到坡下的?上了坡就到家?這是外出辦事或游樂?
夕陽光透過米德蘭大道的叢林,照在他傴背上,其實他沒有停頓,是幾公分幾公分地往上進行,以此狀況來與坡的存在作估量,我也感到坡程之漫長了。
平靜,專注,有信心地移著移著,如果他意識到有人旁觀,也不致認為窺其隱私,他沒有餘力顧及與自己上坡無關的細節。
緊步斜過路面而下,我說了。
他不動,臉色安詳,出言喃喃,指自己的耳朵,微聳肩,那末他是失聰。我改用手勢示意,用目光徵詢他,便見淡漠的唇頰藹然成笑。
試將右臂伸入他左脅、夾緊,使他的體重分到我身上來,我必須稍側,才能用左手去推車子,這就不得不橫著啟步,原以為他受此攙助,便可隨我上坡──一開始動作就知道我想錯了,小病或疲乏的人,才可能附力借力於別人而從事,他是宿疾,胴體和下肢已近僵化,那細小的移步不是他的選擇,是唯一的末技。他瘦瘠,感覺上則比我重,沉重,下墜的陰重。我祗能應和他原來的小步而走,不是走,是移,總比他獨個子上坡要略快一些些。他呢喃問話,我憑猜度而以點頭搖頭來回答他。
首度體識小動作移步的實用況味,平時是每秒鐘一步,這一步,眼下要費七秒許,即以此七個挪動才抵得上平常的一步。挪動之足的踵,不能超過待動之足的趾,只及腳心,就得調換。他需要這樣,因為祗能這樣,我不自然而然地仿效著──紺藍的天,無雲無霞,飛機在高空噴曳白煙,構成廣告字母,那是我感到寂寞而偷偷舉目遠眺了,童年聽課時向窗外的張望,健康人對疾病人的不忠實,德性的宿命的被動性,全出現在我心裏,克制不耐煩,就已是夠不耐煩了。小車受力不均,時而木板滑落,時而提提箱傾歪欲墜──我停下來,先得把車子對付掉。
同意。一從他脅間抽回手臂,立刻感到自身的完整矯健,飛快把小車拉上去仰放在路邊,心想我可以揹他或抱他直達坡端,就怕他不信任不樂意,而我自己也嫌惡別人身上的氣息,人老了有一種空洞的異味,動物老了亦如此,枯木、爛鐵、草灰,無不有此種似焦非焦似霉非霉的異味。
改用左手托其腋脅,右臂圍其腰膂,啟動較為順遂些。不復旁鶩,一小步一小步運作,心裏重複地勸勉:別多想,總得完成,偶然的,別想,完成,偶然‧‧‧‧
終於前面的平路特別的平了,就像以前未曾見過。
他注視我口唇的發音變化,知道我問的是他的「家」,答道:還遠。
再遠也不會遠在瓊美卡之外,何況他的遠近概念與我應是不盡相同。
他只希望再幫助他越過這路到對面去,然後自己回家──表達這個既辭謝又請求的意願時,似乎很費力,以致泪光一閃,暮靄籠著我們,冥青〈這二字原文用字右邊加‘色’〉中感到他是上個世紀的人‧‧‧小鎮教堂的執事,公務機關的謄錄員,邊境車站的稅吏,鄉村學校的業師‧‧‧這四周因而也不像美國‧‧‧我亦隨之與二十世紀脫裂‧‧‧‧
我的呆滯使他阢隉不安,振作著連聲道謝,接住車把準備自己過路了。
我也振作,用那種不自覺的靈活使小車迅速到了對面,用力過猛,提箱之類全滑落在草坪上,就扯了根常春藤,把它們綁在車架上,搖搖很穩實,這些葉子太裝飾性,使小車顯得不倫不類,像個耶誕禮物。
過路時,真怕有車駛來,暮色已成夜色,萬一事起,我得及早揮手叫喊,我們不能加快迴避,該是車停止,上帝,我們不能作出更多。
猶如渡河,平安抵岸,他看出小車被長春藤纏繞的用意而出聲地笑──就此,就這樣分手吧,夜風拂臉,我自責嗅覺過敏,老人特有的氣息總在鼻端,想起兒時的祖輩,中國以耄耋為毂軸的家‧‧‧‧
並立著聽風吹樹葉,我的手被提起,一個灰白的頭低下來──吻手背、手指。
本可就此下坡,卻不自主地走過路面。(小車上的東西有甚麼用,到了家,怎樣的家,他的人,他的一生,他的人的一生──所謂心靈的門不可開,一開就沒有門了‧‧‧上帝要我們作的是祂作不了的事。)
路燈照明局部綠葉,樹下的他整身呈灰白色,招手,不是揮手──他改變主意了,需要我的護送。
奔回去時筋骨間有那種滑翔的經驗。
還是採用一手托脅一手圍腰的方式──被擺脫了。
捉住我的手,印唇而不動‧‧‧涎水流在手背上。
他屏卻我的護送易,我違拒他的感激難,此刻的他,不容挫折──誰也不是施者受者,卻互為施者受者了。
奇異的倦意襲來,唯一的意念是讓我快些無傷於他的離開。
下坡之際,我回頭,揚臂搖手──以後的他,全然不知。
迎面風來,手背涼涼的,摘片樹葉,覺得不該就此揩拭,那又怎樣才是呢,忽然明白風這樣吹,吹一會,手背也乾了。
夏季我慣穿膠底的布面鞋,此時尤感步履勁捷,甚而自識到整個軀肢的骨肉亭勻,走路,徐疾自主,原來走路亦像舞踊一樣可以從中取樂,厚軟底的粗布鞋彷彿天然地合腳愜意。
藉別人之身,經歷了一場殘疾,他帶著病回去,我痊癒了,而額外得了這份康復的懽忻。
他真像是上個世紀留下來而終於作廢的人質,他的一生,倘若全然平凡,連不幸的遭遇〈疾病〉也算在平凡裏,可是惟其平凡,引我遐想──這個遐想隨處映見我的自私。從前,我的不幸,就曾做過別人幸運的反襯。雖然很多不幸業已退去,另外的很多不幸還會湧至。可是那天晚上,我走回來時,分明很輕快地慶幸自身機能的健全,而且慶幸的還不只這些。
後來的每天散步,不經此路。日子長了,也就記不清是哪個斜坡。我感到他已不在人世。(上帝要我們作的是祂作不了的事。凡祂能作的,祂必作了。)
瓊美卡與我已太相似,有益和無害是兩回事,不能耽溺於無害而忘思有益。
我將遷出瓊美卡。
● ( 以上抄錄自木心 「瓊美卡隨想錄」 一書的後記 ) ●
●
維基百科上的木心
●
百度百科上的木心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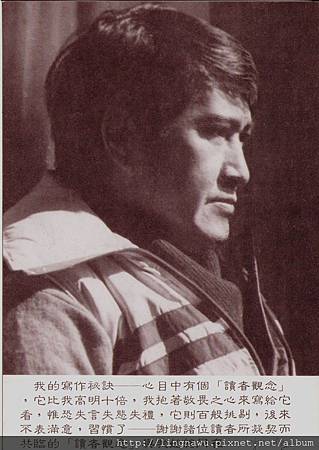


![d4628535e5dde711579eb417a7efce1b9c166187[1].jpg](https://pic.pimg.tw/lingnawu/1443317538-3331648524_m.jpg)
![0df431adcbef7609ffa16c382edda3cc7dd99eeb[1].jpg](https://pic.pimg.tw/lingnawu/1443289019-2827675674_m.jpg)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