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個人各有希望的人生模樣,
一點一滴建構,過程或有辛苦,是值得的安慰。
「安慰」,收在孟若「相愛或是相守」一書中。
故事主要的說書人叫妮娜,溫順的妮娜。丈夫叫路易士,歡樂的路易士。
路易士是位受多數學生敬重的高中生物科學老師,妮娜在同個學校教「拉丁文」,後來拉丁文式微,其實妮娜可以選修幾門進階課程,改教別的課,但她心裡偷偷高興著,可以不必跟路易士在同個地方做同樣的工作。
夫妻倆有位充滿同情心、對甚麼事都能理解、交遊廣闊的友人瑪格麗特。
路易士發現自己患了「肌萎縮側索硬化症」(漸凍人症)而遞上辭呈。
路易士在某次妮娜出門時間吃了藥讓自己死亡。
以下是按原文順序的摘錄
〇那一陣子妮娜下午經常打網球。路易士離開學校崗位,她就不再回學校打球。瑪格莉特說服她,她才又回來打球。
「路易士怎麼樣?」
「愈來愈不妙。」
〇夕陽西下,妮娜想起這個時刻她和路易士散步,從路易士那兒認識一些動物和植物,了解一些生物混雜共生,每天見得到一點點變化,直到寒冬來臨。
〇她出門那段時間,他吃藥了。
他倆討論過這件事,兩人都同意這計畫,但總覺得是未來的事。妮娜本以為她會在場。音樂。枕頭放好,她能握住他的手。但路易士討厭任何儀式。她若參與,也會有後續的麻煩。
〇她查看各處是否留下紙條。沒有。沒有。到處都沒有。
搜過枕頭然後是身體下方的墊子,頭顱發出某種聲音,那聲音和整個展開的床單,彷彿在告訴她不用再找了。
〇他雙眼是闔上的,嘴巴微張,乾乾的,臉容不致扭曲。她才發現改變有多大。之前,他都努力維持某種錯覺,像在說傷害是暫時的,他活力充沛、多少帶點侵略性(儘管已六十二歲)的男性的臉還在。他充滿熱烈情感與生氣的臉,臉上神情每一時刻都在變化,嘲弄、難以置信,有時故作耐煩狀,有時厭惡。可以當作教材。
〇那種病的發病型態分成三種:一是從手及手臂開始,手指變得遲鈍,抓握有困難,最後完全抓不住東西。也可能是腿先變得無力,之後腳步逐漸不穩,很快沒有辦法抬起腳走路,連地毯一小角都可能絆倒一個人。第三種是最嚴重的,咽喉與舌頭不聽使喚,會讓人害怕吞嚥食物,也不見得能吞下去,一嗆到就狠狠地咳嗽,說話像卡住,音節一再重複。
剛開始覺得沒那麼嚴重,既不是心臟或頭腦有問題,而視力、聽覺、味覺、觸覺,最重要的是智力,跟以往一樣活躍。
〇他是從腿開始。他們一知道相關的事實,便開始討論時候到了該怎麼做。他早就說過不見客人。飲食調整,方便吞嚥。他也沒反對買輪椅。她想,是不是重大疾病進展到一半,人會改變,樂觀的情緒往上衝,因為已成定局,不再是抽象的觀念,時時刻刻應付這場病,再也不覺得它討厭。
終點還沒到。活在當下。抓住每一刻。
這不太像路易士的作風。妮娜從沒想過他能夠自欺,而且幹得這麼成功。
〇她翻開電話簿,找到「殯葬業者」。她覺得煩亂無比。轉過頭看他,發現他身上甚麼都沒蓋,顯得那麼無助。她撥電話前,先替他蓋上被單和羽絨被。
〇電話那頭問她醫生去過了嗎?
「他不需要醫生……」
「這樣……,你們的醫生是誰?我打電話請他過去。」
他們不只一次認真討論自殺,但印象所及,從沒談過該不該公開真相。但她相信路易士應該會希望別人知道這件事,那是他做出明智果敢,值得敬佩的決定。
〇「算是幸運了。」醫生下一句話:「要不要跟誰談談,可以幫助妳清理內心的感覺。」醫生和葬儀社搬運工都走了 ─ 路易士被裹得像一件怕被人碰壞的家具 ─ 她得再找找。之前,只知道找床附近,似乎有點笨。過去幾個星期,都是她扶著他移動,但路易士的道別信,可以早早就先藏好。她連錫罐裡的咖啡豆都倒出來找。
〇妮娜身高六尺出頭,當她十幾歲,身邊的人都勸她別駝背,她努力改正但依然駝背。她的父母都是醫生,他們是不會多過問妮娜的。妮娜大學畢業在家鄉一所高中教拉丁文。放假時到歐洲玩,山路上遇到一群做嬉皮打扮的澳洲人和紐西蘭人,帶頭的是路易士。他個頭不高,比妮娜矮個三、四吋,但他黏著人不放。他們結婚,同在一所學校任教。 兩人都有點自負,不想被「媽咪」和「爹地」的身分綁住。他倆深受學生喜愛,尤其是路易士,因為他們不像「家裡的大人」。他們身心活躍,充滿生氣,從生活中找到有意思的事。
〇妮娜加入合唱團,在教會裡辦演唱會。這時她才發現路易士有多不喜歡這種場合。夫妻為此大吵一架。
一個很想找人吵架,一個按捺不住。
「你就不能容忍跟你不同的人嗎?這有甚麼要緊的?」
「如果這不重要,甚麼才是重要?」
她是無法跟他討論的,他們倆的結合太值得感謝,那麼甜蜜又那麼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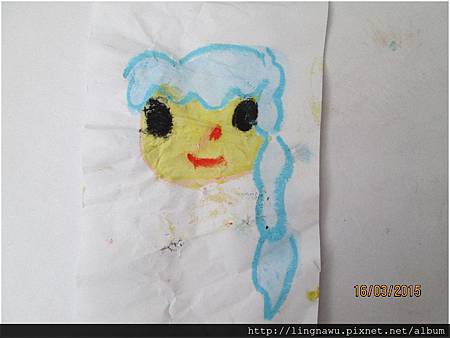
韶安隨意畫
〇幾年前馬路開始出現新的告示牌。鼓吹改建。千萬別墮胎。現在則是《創世紀》的經文。(以前只有「神愛世人」)
路易士說現在有個運動,強調《聖經》上的故事都是真的。
「亞當和夏娃,老掉牙的廢話。」
但他似乎不太介意這個,至少不會比聖誕節時看到大會堂草地上豎立〈耶穌誕生圖〉更冒火。
妮娜屬於貴格會,教義中很少提及亞當夏娃,一回到家把故事從頭讀到尾,前六天了不起的進展讓她感到欣喜:分開陸地和水,造出太陽,月亮,地上爬的,天上飛的種種生物。
「寫得太美了,」她說,「了不起的詩,大家都應該讀一讀。」
他說,地球各個角落都有神話,這是其中之一,沒甚麼比較好或比較差,他受夠了大家都說這首詩寫得多美。
〇「創造論者的傳道」 ─ 一本小書放在路易士桌上或塞進抽屜,他去問校長保羅是哪個傢伙幹的,校長也有收到但不知是誰。路易士提起二位老師的名字說他們是秘密基督徒,保羅說這事不值得如此惱怒,扔掉就是了嘛。
〇在課堂上也有問題。教到「進化論」時,總有面色蒼白的小聖徒女孩或自以為聰明的小孩,搞破壞或曲解。路易士說,如果你們想從宗教觀點了解世界歷史,應該到基督教專門學校……,現在就可以把書收一收,馬上離開,公車可以到。祝你們一路順風,呆……。
針對他是不是說出「呆瓜」,學校分成兩派。就算他沒說,大家也知道他要說的是甚麼。
「我來這裡是教科學,不是宗教。」
「如果你教我們無神論,不等於也是在教某一種宗教?」
「我剛好是教室的老大,教甚麼,我的算。」
「老師,我想上帝才是老大。」
幾個學生被趕出教室。家長來學校反映,校長攔了下來。後來路易士知道了,他說:「要不要放個牌子,此處不許家長與狗進入。」
校長嘆了口氣,依然和顏悅色:「我想他們有權力反映。」
〇開始有信件湧入報社。署名「關心的家長」、「基督徒納稅人」、「未來該何去何從」。信上說,孩子有權在公立學校受教育,無須忍受信仰被破壞或汙衊。反基督的人把持著政府和教育體系,撒旦的魔掌伸進孩童的靈魂。
「撒旦和反基督的人一樣嗎?」妮娜說,「貴格會的人在這方面非常隨便。」
路易士叫她別把這件事當笑話。
「抱歉,」「你覺得牧師在背後操刀?」
路易士覺得是某一組織策動,在總部寫好這些信,以本地住址寄出,這一切並非從他的課堂開始,應該是鎖定了幾所學校,希望在某些方面得到認同。
「所以不是針對你。」
「這樣並不會比較安慰。」
「不會嗎?我以為會。」
〇有人在路易士車上用手指頭沾著灰塵寫上「地獄之火」。有人坐在教室外草地上,當路易士開始上課,他們就朗讀爸媽寫的字條。
校長因不斷的陳情進入學校,而到家拜訪路易士,妮娜端咖啡出來,校長試著捕捉妮娜的眼神,想看出她對這件事的態度。沒用,看不出來。
路易士坐在那裏沉默良久,讓人以為有希望了。後來才知道,沉默只是伎倆,讓人知道這些提議有多不合理。
〇路易士也寫信給報社。說明和宗教「演化論」不同的,科學的「進化論」。
報社編輯不是本地人,才剛從新聞學校畢業,吵得愈兇他愈高興。
〇路易士寫了辭職信,理由是健康欠佳。他發現自己感覺不到腳。如果有地毯,一點點皺角就足以絆倒他。掉落地面的一截粉筆或鉛筆就成為災難。
〇湖濱葬儀之家,現在已經翻修為一棟金磚蓋成的新大樓。老闆是接班的新一代布魯斯,以前和兄弟以及父母親(艾德和凱蒂)住在二、三樓。現在父母住到鎮上去,真的忙到不便回到鎮上,布魯斯還是睡在樓上保留的房間。
「斯比爾先生教我十一、十二年級的科學,他是令人難忘的老師。……,妳要我先跟妳解釋流程,還是想先看看妳先生?」
「我們只要火化。」她說。
「對,然後就會火化。」
「不,他應該立刻火化,這是他想要的。我是來拿他的骨灰。」
「我們沒收到這種指示,已經整理好大體,可以給家屬看,他看起來很不錯……。」
她站在那哩,瞪著他。
「應該有打算讓訪客致意吧?我們不涉及宗教,只唸一段頌辭……。」事實是,他們完成所有該做的工作,沒有人告訴他們不必做,這是要付錢的……。
一部車停在外面,愛德來了,布魯斯大大鬆了一口氣,這一行他該學的還很多。
愛德說:「哈囉,妮娜,我看到妳的車,我想我該進來告訴妳,我很難過。」
〇妮娜一個晚上都待在起居室。睡眠很淺,不斷想到自己躺在沙發上,而路易士在葬儀社。
在葬儀社,她想開口講話,但她總是打顫發抖,說得支離破碎。可怕的哀憐。但這不是她內心真正的情緒。
愛德把妮娜帶出葬儀社,
「我不知道怎麼了。」妮娜說。
「嚇壞了。」愛德從口袋掏出東西,是一張摺得很小的紙條。
「我替妳留著這個。」,「在他的睡衣口袋。」
睡衣口袋,唯一漏掉的地方。她沒碰他的身體。

韶安的偶拾
路易士留給她的是一首詩(讓她找得好辛苦),一首尖酸的打油詩。
題目:上帝創造論者與達爾文後代的戰爭,為了這一代的軟弱靈魂
休倫湖邊蓋起一座
學習的神殿
好多兩眼呆滯的學生來到這兒
聽一群蠢貨講課
這群蠢貨的領頭是個好傢伙
笑到嘴巴合不攏
這廝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
講點他們愛聽的當作呼弄
〇某年冬天,瑪格莉特安排一個聚會,讓大家聊聊自己感興趣又了解的事。除了「老師」也邀「一般人」,每個人帶一道菜參加。
凱蒂和愛德是這個團體裡的「一般人」,他們是瑪格麗特的鄰居。有次,愛德講登山,他走過洛磯山脈,喜歡分享他閱讀的山難故事。(瑪格麗特喝咖啡時以開玩笑口吻跟妮娜說:「我本來擔心他會講屍體防腐。」妮娜咯咯發笑說:「也許他想感興趣的人不會多。」)
愛德的妻子凱蒂是個甜蜜的人,對她的婚姻、孩子、一年的四季、鎮上,尤其是宗教,都熱情洋溢。特別喜愛神秘儀式,比如產後婦女的「安產禮」。瑪格麗特和妮娜覺得超過,路易士則認為她有問題。不過大部分人都被她迷住了。
〇在瑪格麗特家的聚會,可想而知,凱蒂和路易士的問答會是如何激烈,要不了多久在場每個人都聽到了。
妮娜避難到廚房,把滾燙的臉頰貼在窗玻璃上。愛德也來了。他們彼此笑了笑,簡短和善略帶抱歉但與我無關的笑。許多事,盡在不言中。
他們暫時丟下凱蒂和路易士。
(路易士氣勢洶洶,而凱蒂為路易士感到悲哀,他們倆自我感覺好得很。)
愛德和妮娜靠在一起,至少他們都討厭爭執不休。過分積極,從不肯放鬆的性格,令人疲倦。
〇高中的校長保羅沒想過妮娜竟然有意見,他一直覺得她很有人情味,不像路易士全身都是刺。
「路易士他舉足輕重,很多人想向他告別,向他致敬。完全沒有宗教儀式,沒有禱告沒有表揚,最後由我作結,代表大家的『感謝辭』……。」
「路易士不要這些。路易士死的時候留下一首詩,如果你可以接受,我就出席。」她在電話中讀出這首詩。
〇她在生自己的氣,跟保羅在電話中的表現不夠好,太像在演戲(保羅說妳得壓下來)。憤怒是路易士的一切,復仇是他的強項,她只能引用他的話,被奪走了他的她。
〇天黑之後,愛德敲她家後門,一盒骨灰,一束白玫瑰。
該放哪裡好?餐桌上?不好。流理台?感覺像雜物。地板?感覺不太尊重。
最後她把骨灰放在比較矮的電話桌上。
那束白玫瑰,是給誰的呢?可能是給這屋裡的死者。她開始找花瓶。
她問:「路易士口袋裡那張紙你有看嗎?」
他搖搖頭。他撒謊。
她想告訴他,路易士的遺言,讓她驚訝,也讓她的心都冷了。
〇妮娜與愛德,這些年來相安無事,因為兩人都有婚姻。對兩人來說,婚姻是生活的實質內涵。儘管她與路易士的婚姻讓她覺得難受、難以理解,但她的人生無法脫離它而存在。即使兩人都恢復成自由身,但並不等於歸零,危險將在於嘗試經歷過以後,發現就那麼毀了,然後想,原來真的是零。
他們在桌邊坐下。
妮娜問的是:「你昨晚對他做了甚麼?」,「如果你介意,可以不用回答。」
「我很驚訝妳問這個,」(愛德回答了屍體處理的過程,非常仔細的。就有評論家評論孟若以深度和廣度的知識寫小說,讓人如同在場。考慮再三,略。)
〇他走了以後,她帶著骨灰,向鎮外開去。在一個交叉路口停車,往旁邊的小路走去。她聞到馬的味道,沒錯,附近視線所及有兩匹馬,牠們站著理毛,靠在對方身上,看著她。
她打開盒子,把手放進骨灰 ─ 當中混著小小的,依舊頑抗的碎骨 ─ 將骨灰撒在道旁植物周圍。這麼做就像在六月天第一次縱身跳入湖泊游泳,感受其間的冰涼。一開始是令人作嘔的驚嚇,接著對自己還能動感到驚異。
鋼鐵般的愛浮出湖面,平靜地俯視人生的表面,儘管寒冷的痛苦不斷淘洗著你的身體。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